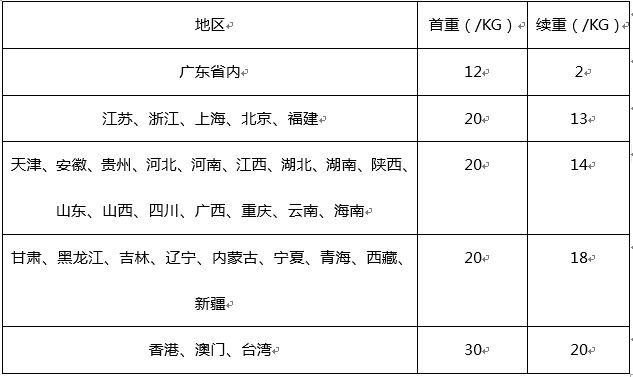马骏:上行和下行风险 应该永久性取消GDP增长目标
2021-01-28 16:59:51来源:第一财经
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
一是基准预测,即我们目前认为的大概率情况;二是上行和下行风险。
基准预测方面,2021年我们基准预测在8.5%左右。2021年的数字里面有很大的基数效应,即去年一季度非常低,这种统计上的基数效应容易给投资人、政府部门带来误导,包括对宏观政策的误导,因此要加以关注。
下行风险方面,最不确定的还是疫情,疫情是否会有比较大的反弹,现在还不清楚。如果出现明显反弹,今年前几个月可能会重新面临一些经济下行压力,尤其体现在零售、旅游等方面。国际上的情况更不确定。一个多月以前,我听一些国外专家讲,基本上OECD国家上半年能打疫苗,打完疫苗就可以自由流动了,现在这种观点已经慢慢被抛弃。哈佛大学专家做了一个非常悲观的预测,认为疫情要延续到2025年。
根据这类观点,疫苗不可能在全球覆盖全民,只要有人不打疫苗,就没有完全保护。另外,疫苗平均只有80%左右的有效率,对变异之后的病毒疫苗也不能有效对应。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对国际旅行的限制很可能是长期解除不了的,这对我国的外贸投资和技术合作等都有很大的影响,国内的疫情防控也会是时紧时松,间歇性地对经济造成冲击。
其他下行风险主要集中在金融相关领域。首先是地方债务的风险。虽然财政刺激力度不小,但去年许多地方的财政状况是在恶化的,尤其在中西部、东北。其次是小银行的风险,虽然小微企业得到了很大救助,但是总体来看小企业的违约风险还是在上升,小银行主要发放小微企业的贷款,所以其资产质量在下降。另外,大银行去年在小微企业贷款方面增长非常快,许多质量好的小企业变成了大银行的客户。另外就是债券违约的情况,虽然应该从规范行为方面强调不能逃废债,但是有些地方和企业真是盖不住了。这些都是要关注的下行风险。
上行风险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可能是在中美关系。拜登即将上任,美国一些分析家认为,新的美国政府可能愿意在三个领域和中国合作:一是应对气候变化,这个领域较大,从我们绿色产业的定义来看,包括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制造业、林业等,如果把它充分展开的话,总共有211个类别。二是与疫情有关的公共卫生的合作,与医疗相关的一些产业可能会因此受益;三是防止核武器扩散。此外,中美贸易僵局在某些领域也可能有缓解的机会。
“十四五”期间是否要设立GDP增长目标
我的观点是不要再设GDP的增长目标了。2020年初的时候,因为疫情带来巨大不确定性,无法定这个目标,定得太高,做不到;定得太低,起不到提振信心的作用,所以没有必要设。去年政府工作报告决定2020年不设当年GDP增长目标,是非常正确的,是以“民生为本”治国理念的优秀案例。
我个人认为,从今年开始应该永久性取消GDP增长目标,而把稳定就业和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政策最主要的目标。GDP数字可以作为一个预测,财政部门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基础来进行财政收支的预测,投资部门可以将其作为基础来预测投资行为,但不应该将其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业绩的指标。继续设立GDP增速目标的问题包括:
第一,如果GDP增速是一个官方目标的话,就可能出现地方习惯性的层层加码,把地方GDP目标定得很高,从而加大隐性债务的金融风险,因为靠借钱来实现投资拉动GDP比其他办法都容易。
第二,强调GDP考核,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地方虚报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
第三,2020年GDP增长速度存在很大的基数效应,因为这个基数效应,今年GDP可能达到8.5%,那是否应该把2020年的目标定到8.5%?假如定了,2021年突然掉到五点几,解释起来就很费劲。
第四,把稳定就业、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市场经济下各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普遍做法。现在,所有发达国家和绝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都已经放弃了GDP增速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
货币政策应适度转向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悖论,一方面杠杆率上升得非常快,要求货币政策开始调整。2020年前三个季度,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25个百分点,是2009年以来升幅最高的一次。杠杆率大幅上升,自然会导致金融风险。此外,有些领域的泡沫已经显现,去年我国几个主要股市指数都大幅上升,接近30%,在经济增速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出现如此牛市,不可能与货币无关。另外,最近上海、深圳等地房价涨得不少,这些都与流动性和杠杆率变化有关。未来这种情况是否加剧,取决于今年货币政策要不要适度转向,如果不转向,这些问题肯定会继续,会导致中长期更大的经济金融风险。
悖论的另一个方面即货币政策转向不能太快。目前我国通胀不高,CPI今年看上去会更好看,因为去年的猪肉基数效应。PPI会往上涨,但不会涨得太多,也没有要求一定要转得太快。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强烈要求要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或者要求转得非常慢,认为转得太快会导致项目停工、烂尾、坏账等问题。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1年要“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这个意思是宏观杠杆率不要再升了,但政策也不能急转弯。
但是,M2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如何跟名义GDP匹配?“匹配”是写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里的,但是有很大的诠释空间。至少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把今年的名义GDP增速理解为包括了基数效应的名义GDP增速。实际GDP增速大概是8.5%,加上两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率,名义GDP增速就是10.5%左右。今年M2要不要增长10.5%,如果要的话,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字。
第二种解释,是把一次性的基数效应剔除后正常化的名义GDP增速。我估计大概要剔掉三个百分点,这样今年的名义GDP增速就变成7.5%。今年M2增速到底是匹配10.5%还是7.5%,就看怎么解释了。如果是10.5%,那是一个扩张性的增速;如果是7.5%,那是比较紧缩性的,两者货币总量相差6万亿元。我的观点是在中间取一个数,比如控制在9%左右,相对来讲比较合理。
有几个理由。第一,今年企业盈利状况会有很大好转。很多上市公司预测今年有20%以上的盈利增长。由于盈利变好,一些企业是有望通过盈利来进行再投资的,因此可以相对减少对债权融资的依赖,从而可以略微降低杠杆率,对货币扩张的压力会有所下降。
第二,货币条件要适应广义财政赤字调整。去年我国广义财政赤字(包括一般预算赤字、特别国债和地方专项债)估计是8.3%的GDP,我认为未来两三年内广义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应该逐步回归到疫情前的水平(如2019年的水平)。广义财政赤字下降,政府发债没有那么多了,自然会减少对货币政策扩张的压力。
第三,是基数效应问题。去年我国实体经济上半年基数很低,使得今年上半年GDP增长速度会很高。但是从M2的角度而言,正好反过来,因为去年上半年货币扩张很快,今年会有一个基数假象,让大家觉得今年上半年的M2增长同比速度比较低。我认为要剔除这个假象来看货币充裕度,因为基数已经很高了,在这个基础上再增长8%~9%也是不小的数字。
应放松对外汇流出的具体管控措施
人民币从去年年中开始已经升值将近10%了。如果再升值5%以上,就可能对出口部门产生明显压力。
让人民银行通过干预外汇市场来调节汇率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与以供求为基础决定汇率的市场化原则是相悖的。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应该积极考虑适当放松对外汇流出的一些具体管控措施,让一些外汇流出境外,减少人民币升值压力,同时利用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机遇为下一步人民币国际化提供铺垫。
我的具体建议包括,简化对个人换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境外留存外汇的外汇管理方法,取消QDII的额度限制,加快“债券通”框架下境内投资者投资海外债市的通道建设(可以考虑“南向通”投资标的包括中国香港之外的国际债券市场)。
碳中和与绿色金融体系的完善
易纲行长最近多次强调要围绕碳中和目标,完善绿色金融体系,这将成为人民银行今后一段时间内的重要工作任务。我认为碳中和会给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机遇。这个机遇的规模有多大?生态环境部气候变化事务特别顾问解振华带研究团队进行了测算,认为碳中和在未来几十年会带来138万亿元的低碳投资需求。我从去年开始给重庆做一个碳中和与绿色金融路线图的研究,结果显示,重庆一个省级经济体在未来三十年就需要8万亿元的低碳投资(按2018年不变价计算)。重庆占到全国的GDP大概1/40,其人均收入和全国平均水平差不多,如果乘上40倍就是几百万亿元的概念,这是非常大的数字。金融机构如果不认真研究碳中和,可能就失去了在未来金融领域发展的最大机遇。
同时要防范气候转型带来的风险,因为未来所有高碳产业都可能出现许多坏账。举一个例子,我牵头的研究团队做了对煤电行业贷款违约率的预测,煤电贷款违约率现在是3%左右,十年之后会变成20%以上。因为碳中和意味着政府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削减对高碳能源的需求,减少用煤电,更多利用新能源。同时由于技术的进步,像光伏、风电等能源的发电成本大幅下降,未来会降到煤电成本的一半以下。如果没有可商业化的碳捕捉技术,这些压力会导致煤电这类高碳能源和其他高碳产业(钢铁、水泥、铝业、石化等)企业出现很高的违约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领域,是我们在低碳转型过程中要防范的重大风险。所以,碳中和一方面是机遇,一方面是风险。
我认为,金融体系支持碳中和的目标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是要修改绿色金融的支持目录。现在有三个目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和绿色产业,分别由银保监会、人民银行、发改委牵头制定。只有最新的绿色债券目录征求意见版把清洁煤这类高碳项目剔除了。清洁煤虽然能够降低空气污染,但是不能减碳,是和碳中和目标相违背的。未来绿色金融的各类标准都不应该支持高碳项目。
第二,要建立强制性要求金融机构披露气候信息的制度。银行贷款到底产生了多少碳排放,必须进行估算和披露。如果金融企业不知道其所支持的项目碳排放强度,就无法实现碳中和。未来这类信息披露应该变成强制性要求。
第三,金融机构要开展环境气候风险分析。金融机构要判断环境高风险领域中投资和贷款会出现多高的不良率,会出现多少资产减值。这就是环境或气候压力测试,是传统的财务压力测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
第四,要强化对绿色低碳投资的激励机制。一是可以设立更大规模的绿色再贷款机制。原来也有提绿色再贷款,但它只是再贷款中的一部分,不是专门的绿色再贷款。未来应该考虑把每年几千亿元的低碳项目作为再贷款支持的对象。二是把较低风险的绿色资产,包括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作为央行的合格抵押品。三是央行要评估商业银行的碳足迹,主要是银行贷款的碳足迹,并以此作为给银行提供低成本资金的参考依据。
第五,外管局和主权基金也要开展绿色投资。国际上很多资产拥有者先行变得绿色化,然后通过自身的绿色偏好影响资产管理人。外管局和主权基金应该按可持续/ESG投资原则建立对投资标的和基金管理人的筛选机制;建立分析环境和气候风险的能力;披露ESG信息;投资和支持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发挥股东作用,推动被投资企业提升ESG表现。
第六,强化碳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碳市场应该发挥碳定价的作用,使有流动性支持的碳价成为引导各行业进行低碳投资的重要市场信号。应该支持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参与碳市场,提升流动性,保证碳定价的有效性,开发碳排放期权期货等衍生产品。

 免责声明
免责声明